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NT同龄人的3倍
——美国丫丫爸爸

作者简介
Emily Sohn
Emily Sohn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位自由记者。她主要报道健康、科学、探险等话题。她的作品发表于《自然》,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杂志。

本文对霸凌和身体心理的虐待的描述可能会令一些读者感到不适。
霸凌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会发生。
Kassiane Asasumasu依然记得,在5岁的时候,其他孩子就会随意拿走她的东西,并且因为知道她脸盲,无法告发他们而撒谎抵赖。十岁的时候,在一场睡衣派对上,女孩们不停嘲笑她,把她的内衣裤塞进冰箱,还比赛,看能够让她哭多少次。在睡衣派对后的48小时,她一直处于崩溃状态。
接下来的一年,同学们将她锁在一个储物柜中,然而学校却因为她踢坏了储物柜的门而惩罚她。Asasumasu在3岁时被诊断有自闭症,她说:“我大部分的童年记忆都是,其他孩子的刻薄。小学时每天都在哭泣。”有时候,她哭得太厉害了,以至都吐了。没有被弄哭的时候,也是遭受各种侮辱。
中学时,老师们不断告诉她的妈妈,说她有自杀的倾向。这对她而言,却是记忆中大人对她的唯一的关注。老师要求她忽略那些针对她的折磨,可是她实在无法做到。她依然记得,在家的时候,她的七个兄弟姐妹经常调皮捣蛋,却将一切错误加到她头上,而她的父母从来也不问青红皂白地责罚她。
现年37岁的Asasumasu说:“我总是不断替人背黑锅。”许多自闭症人士都经历过Asasumasu一样的可怕的霸凌。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被霸凌和身体甚至性虐待的几率,是NT同龄人的三倍。这样的虐待让他们遭受严重的压力和创伤,而这种虐待却往往不被认识到。帮助治疗自闭症人士创伤的方法,目前大多还是实验性的,因此,谱系人士往往就只能各安天命了。
Christina McDonnell,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布莱克斯堡州立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助理教授,她指出:“遭受虐待或任何形式暴力的自闭症儿童都是非常弱势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更有可能遭遇这些虐待经历,而且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帮助他们。”包括她在内的专家都认为,建立更好体系来帮助谱系人士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亲耳聆听他们受伤害的经历经验。
虐待包括遗弃、感情、身体和性方面的虐待。数十年来的所有研究都表明,残障儿童特别容易受到虐待。但是专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则很少。
2014年,McDonnell还是一名研究生,专门研究儿童虐待问题的研究生,她发现,在美国国家社会服务部的调查报告中,大部分的儿童虐待案例中,都包括有自闭症等残障儿童。但是检索科研文献,她却发现了文献与实际案例不一致:虐待带来的创伤性压力研究中,很少考虑儿童的自闭症诊断。
而研究自闭症的学者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受到的虐待。零星的几项研究,结果各不相同。一些研究认为,自闭症儿童比NT同龄人更容易被忽视或被虐待,并且更有可能列为儿童保护的服务对象(美国国务院的一项针对监督儿童福祉的项目)。其他研究则没有发现自闭症与被虐待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些研究都有种种局限,包括接受访谈的样本过小或者使用了早期的自闭症诊断标准。
McDonnell和她的同事决定研究这种联系,收集了南卡罗来纳州自闭症普查数据和社会服务部的案例。他们比较了1992年至1998年出生的近5,000名儿童(包括有和没有自闭症)被虐待和忽视的样本。他们发现,该州近五分之一的自闭症儿童、以及三分之一同时有自闭症和智力障碍的儿童,受到过虐待。研究小组在2018年报告指出,即使消除了诸如低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自闭症儿童遭受虐待的可能性仍然是NT同龄人的三倍。McDonnel说:“这些数字已经够令人震惊了,而且居然如此之高。”
对于自闭症儿童以及智障儿童而言,忽视尤其是个问题。位于哥伦比亚的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工作学助理教授Kristen Seay指出,忽视是儿童保护服务所记录的最常见的虐待类型。更严重的是,自闭症儿童往往有更多的需求,但这是那些资源匮乏的家庭所难以满足的。
McDonnell的小组发现,自闭症儿童也更容易遭受身体虐待。直系亲属中的主要看护人是最常见施虐者,但是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保姆和保育人员等,都可能会虐待自闭症或智障儿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田纳西州。那里的研究者分析了当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自闭症监测站点的数据,发现在被转介到儿童保护服务里的儿童,自闭症儿童的比例是普通儿童的两倍还多。
这项研究包括了2006年出生的24,000多名儿童,在田纳西州的儿童虐待热线的举报案例中,387名自闭症儿童里,有17%的儿童受到虐待,而其他孩子中这一数字则为7%。尽管报告的数量较多,但是,儿童保护的专业人员仅对62%自闭症儿童的照料者进行了调查,而对普通儿童的则为92%。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首席研究员Zachary Warren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提高认识,因为这代表了一群极其弱势的群体。”

Nancy Nestor的儿子P.(为了保护其隐私,我们仅使用P.的首字母缩写。)3岁的时候,从幼儿园回家,在自己的房间,一边玩一边喃喃自语着“ 笨蛋P。笨蛋 P。”(P.在4岁的时候诊断有自闭症。)那时候,P.并不知道“笨蛋”是什么意思,但Nestor却伤心欲绝。她向老师反映了这个事情,老师也感到震惊。老师表示没有听到学生说这个词,但是答应她会留意,就草草结束了这个话题。但是Nestor仍然担心:她儿子不太会表达,所以无法告诉她,这样霸凌的行为是否还在继续。她说:“没有人愿意听到别人称自己的孩子是笨蛋,尤其是对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在随后的几年中,P.偶尔会遇到各种霸凌,包括一群高中生把揉成一团的午餐纸袋扔给他,让他扔掉。但是,他也得到了同学、当时田径队队友和教练的同情和支持。P.现在22岁,就读于社区大学并住在家里。Nestor仍然在认真聆听他的自言自语,以了解他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Kennedy Krieger研究所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Daniel Hoover指出,同龄人的身体攻击可能造成自闭症儿童的脸部受伤,肩关节脱位,并且在他们身上留下很多的抓痕。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 Hoover和同事综述了许多研究报导,发现,自闭症儿童被霸凌(包括其兄弟姐妹的霸凌)的几率是其他儿童的三到四倍:40%至90%的自闭症儿童有被霸凌的经历,而普通儿童则为10%至40%。
有时候,孩子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父母却会发现自闭症孩子被霸凌的迹象。例如,P.上小学时,在和同伴玩“警察和小偷”的游戏,他总是被当作囚犯。几年后,一本中学年刊中,有一张P.被关在笼子里的照片,那是他们去佛吉尼亚威廉斯堡市的早期移民博物馆野游的照片。这张照片刺痛了Nestor,因为当时的情景肯定得到了多位成年人首肯。Nestor感觉,P.被所有人当作了“怪孩子”而被关在笼子里。Nestor说:“这不是明显的霸凌,但歧视是必然存在的。P.当时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玩。”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一些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比他们的父母对于霸凌行为更加敏感。大约两年前,Hoover帮助过一位自闭症少年。因为一个同学调侃了他最喜欢的职业橄榄球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而倍感沮丧。而让他抓狂的仅仅是,那位同学说了“放气门”,意在讽刺2014年的一场季后赛中,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Tom Brady被指控,要求给当时的比赛用球放点气。Hoover回忆说,这个孩子“当时无法保持正常,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对于一般人来说,说一个橄榄球队的垃圾话,更多的是无恶意的玩笑,而不是霸凌。但是,对这个男孩来说,却非常受伤。
一些自闭症人士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时时感到压力,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真实而实在的。他们无法理解人们在说话或办事方式上的细微差别,特别是别人言行不一的时候,更让他们不能信任任何人。心理学家Connor Kerns指出,“因为不明白那些社交暗示,大多数时候,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你总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周遭充满压力,这些都能造成长期的、潜在的创伤。” Connor Kerns是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焦虑压力和自闭症项目的负责人。
研究表明,相对于那些活跃和外向的孩子,内向或焦虑的孩子更容易在受到虐待后造成心灵创伤。缺乏社交网络可能会加剧该问题。专家指出,没有智力障碍的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与智力障碍的儿童相比,他们对人际差异的了解和社交敏感性更高。更糟糕的是,许多自闭症儿童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迅速做出强烈反应。Hoover指出 “他们气坏了,吓坏了,乱跑,大喊,变得很生气。而这反过来也可能引起其他孩子的强烈兴趣,变本加厉地霸凌他们。”
施虐者选择自闭症儿童作为目标有自己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自闭症谱系儿童往往缺乏沟通能力,无法报告这些虐待行为,或者报告了,大人也不相信他们。Seary记得一位发育障碍的年轻女孩,告诉家人在学校被性侵。女孩的父母告诉学校行政人员,但是双方都对她的故事表示怀疑,直到一个她的一位NT妹妹也报告说,她也被性侵了。对姐妹俩的体检证实了她的说法。Seary指出“虐童的人知道,哪些儿童是更好的施虐对象——什么也不会说的,有交流困难的。即便受害者去报告了,他们也会指出,这个孩子以前撒过谎。”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接受特殊教育的自闭症儿童,会接触更多的成年人,从而增加了他们遇到施虐者的机会。
Corr教授指出,自闭症儿童持续受到虐待的原因,也可能是老师没有受过培训,不能甄别儿童受到虐待的迹象,或者害怕说出来,会使孩子们的情况变得更糟。她说:“通常的担心是,向儿童福利系统报告残障儿童受虐待的的情况,反倒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儿童福利工作人员,并不一定接受过专门的针对残障儿童的培训。孩子一旦进入他们的系统,寻求保护,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这些孩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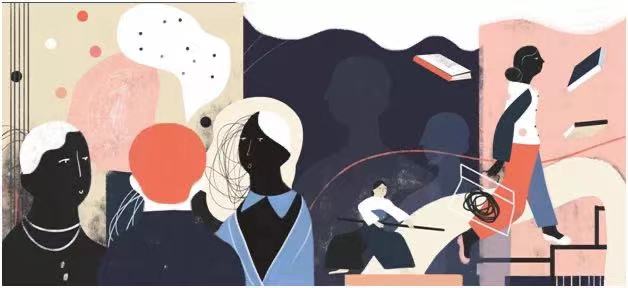
Asasumasu最早、最痛苦的记忆是,在3岁的时候,就必须忍受,双腿被一位老师绑在童椅上,以防止她随意走动。老师给出指令,“坐下、站起来、看着我。”如果Asasumasu听从指令,做了这些动作,她将获得一小块的M&M糖。如果她不配合,老师则拉伸她的身子,或强迫她睁开眼睛。
这个干预技术是自闭症标准干预方法的一部分,引起了争议。批评者将其与虐待关系中的煤气灯效应相提并论,因为它教育孩子们遵守并执行特定的行为以获得奖励,而不是在感到不适时大声说出来(译注:煤气灯效应,是一种心理操纵的形式,其方法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隐秘地让受害人逐渐开始怀疑自己,使他们质疑自己的记忆力,感知力或判断力,其结果是导致受害者的认知失调和其他变化,例如低下的自我尊重。最近常见诸于各大新闻的PUA,即采取此办法)。许多成年人一直对他们在孩童时期接受这种治疗的创伤记忆大声疾呼。“我最早的记忆是大人们强撑着我的眼睛,让我看着他们,”Asasumasu说:“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说‘看着我’,就像‘我再也不会看着你了。’”
虐待会导致持久的伤害,导致严重的压力、沮丧、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目前,大多数研究尚未证明自闭症人群中PTSD的发生率增加。Kerns说,这可能是因为PTSD的诊断标准不是为自闭症人士编写的,或者自闭症人群受到创伤后不容易造成PTSD,而是更容易导致焦虑、抑郁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并没有可靠的方法去筛查自闭症儿童的创伤——应激创伤的定义是一种或多种对人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有时会持续发生。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正在设计干预方法。例如,Hoover教授正在采用一种注重防止创伤的认知行为干预技术。这项为期12周的项目,旨在帮助孩子们谈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并教他们如何处理这些经历中所面临的恐惧。考虑到许多自闭症儿童可能不能理解语言指令,或者在干预完后,忘了怎么进行练习,Hoover为他们制定了在家中练习的视觉提示表,鼓励家庭更多地参与。改进后的项目还使用了儿童的感兴趣的元素,例如蜘蛛侠或哈利波特,来帮助他们回忆自己的经历。
Hoover认为,这改进的方法,至少家长们认为,似乎有帮助。父母们都报告了积极的效果,接受干预的自闭症儿童在UCLA儿童/青少年PTSD反应指数上的得分也有所提高——该指数是一个自我报告的调查表,用于筛查儿童和青少年的PTSD。Hoover正在为这项技术编写手册,并透露他每周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要求培训的咨询。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和同事收集了几十名儿童的干预数据,并计划进行一项对照试验。
与此同时,McDonnell正在制定针对自闭症儿童遭受创伤的评估方法。其他团队正在尝试社区和草根组织的项目,给大家灌输有关虐待、性暴力和其他虐待方式的知识,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许多自闭症人士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现年36岁的Adrienne Lawrence是加州洛杉矶的一名律师和作家,大约一年前才知道自己有自闭症。但是她很早就知道,自己解读世界的方法,是逻辑推理,而不是观察各种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细微差别。例如,如果一个与她约会的男人说,他的母亲去世了,那么她很直接地认为,他只是想告诉,他母亲去世了,却无法领会到,他其实是想引起她的同情心,从而两人能够呆在一起过夜。如果他道歉并保证自己不再撒谎,她会认为他是认真的。Lawrence认为,自闭症人士遭受如此多虐待的原因是,很多没有自闭症的人士总在撒谎,而不是自闭症人士会不能解读那些谎言。
Lawrence一直在给自己创造规则来帮助她解读世界,在知道了自己有自闭症后,又采取了一些新规则。例如,她过去工作中曾遭受到性骚扰,于是制定了具体的准则,来帮助自己发现并避免性骚扰,这些准则细化到在不同的情况下,哪些行为是合适的。“以前,我会用我10年犯罪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统计和逻辑分析,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安全进入一个男人的家里。当然,我现在不必过于依赖统计数据和逻辑思维,而只是确保所有会面都在公共场所进行。”
对于Asasumasu来说,她在高中的时候学会了反击,生活才开始好转。她还与她认为同样“怪异”和“可怕”的学生成为朋友,从而远离了霸凌。尽管她成年后还继续受到虐待,但是,她正在学习合气道,这种防御性的搏击术帮助她,在判断某种情况十分构成威胁的时候,可以先耐心地评估一下。
和Lawrence一样,她也依靠模式识别来预测和逃避虐待。她指出:“那些对餐馆服务员无礼,对宠物很残忍的人,肯定会在某个时候试图打击你。”
Asasumasu指出,最终必须改变的是社会,而不是自闭症人士。她说:“我们应该能够接受人的多样性存在的事实。对于在大千世界中的各种文明用语中,你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话‘嘿,在面对和你不一样的人时,能不能不那么混蛋。’”
-
原文发表于美国西蒙基金会网站,小丫丫自闭症项目获得该网站授权翻译。
-
原文链接:
https://www.spectrumnews.org/features/deep-dive/how-abuse-mars-the-lives-of-autistic-people/
-
小丫丫自闭症项目并不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但是,本着尊重原作者,尊重西蒙基金会的原则,我们忠实翻译全文。——美国丫丫爸爸2020年于美国圣路易斯。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小丫丫自闭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