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我被诊断自闭症
文 | 星星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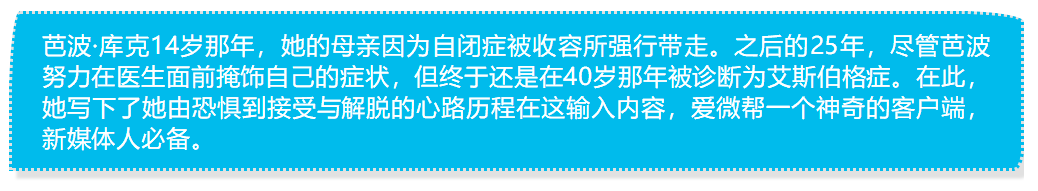
目睹母亲熟睡的身体绑在担架上,被抬下楼塞进一辆救护车,我感觉就像在观看一部默片的慢动作。我努力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把她带走呢?
我父亲坚信她“疯了”,所以把她交付给了一家精神病院。
母亲一直有些不正常。她不大会社交,没有朋友,也不喜欢被摸或者拥抱。
多年以后,我终于懂得了父亲关于她不够女人的说法。
三天之后,我们得以去看她。一座80年代的精神病院不是一个14岁的孩子应该踏足的地方,它难以置信地令我害怕和沮丧。
妈妈见到我们很开心。“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我都可以回家了!”她声称。
我忘不了当她的请求被拒绝时她的脸庞,她立刻大闹了一场,而这是她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她被拖走、灌药,直到她真正的自我泯灭殆尽。
之后逾15年,医生为了找到一种有效的药物组合,让她持续服药。其中一种组合让她精神错乱,然后从楼顶跳下。在经历了18次电休克疗法之后,她彻底迷失在了自己的世界当中。
最后,在使用一种有毒的药物组合之后,母亲结束了她悲剧的一生。
她终于得以从精神病院的折磨中解脱,而我则怀着对心理健康组织和专家的深深恐惧逐渐长大,同时,我也害怕自己也会患有精神分裂症,躁郁症( 抑郁狂躁型忧郁症 )或者偏执狂(就像他们误诊母亲一样)。
我这一生都在努力融入社会。各种社交场合让我不知所措,而眼神交流则让我痛苦。人们说我“高傲自大”,可是事实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人交谈。
我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而我更害怕被关进精神病院。
在90年代中期,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保罗。他理解我,而我也理解他。多年以后一则关于抽动秽语综合症的广告才令我怀疑我们两人是否正常。
现代技术使得搜索信息变得更为便捷,于是我很快意识到保罗可能患有自闭症,而许多的症状也向我敲响了警钟。
“自闭症”这个词曾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说话的人拍着手在墙角摇晃,完全从外界隔绝。
我从未意识到自闭症的的症状可以如此不同。我们花了许多天在网上搜索,从图书馆借阅书籍,甚至还观看了一部讲述一对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的夫妻的电影---《莫扎特和鲸》。我们像是经历了一次情感的过山车。
一天晚上,保罗在做饭时崩溃了。在这一切的沉重负担让他双腿无力支撑。在某种成程度上来说,这就像经历了悲痛的五阶段:怀疑,悲痛,愤怒,绝望以及最后的接受。
我们都去咨询了心理医生。保罗很快被诊断为艾斯伯格综合症,然而我一开始却被诊断为躁郁症。
我可能要在精神病院了却余生,这个念头让我害怕。我绝望地离开了诊所。当时我还不知道患有自闭症或者艾斯伯格综合症的女性常容易被误诊为躁郁症或者人格障碍。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终于得以理解自我,变得乐观,而我,自觉难逃厄运。我没有想到我可能是被误诊。
六个月后,我们去看了另一个全科医生。她快速地确认我没有患躁郁症。她观看了我和保罗之间奇怪的交流(互相接对方的话茬,完成对方的句子),然后把我交给一个心理医生。
我被录像,填写问卷,写了一篇有关我童年的短文,完成阅读和跟踪测试。这些显示,智商超过150的我有一定的学习障碍。我最后的诊断是艾斯伯格综合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
在测试的时候,我被告知,我的艾斯伯格综合症症状有所“不同”,不过,女性艾斯伯格症的诊断标准正在酝酿之中。而由Tony Attwood教授设计的一项新的诊断工具将极大地改进诊断过程,为广大女性免去被误诊带来的伤害。
终于,我也接受了自我。我们都知道得了我们是谁,这几乎为我们人格重新赋权。我们不再听从那些否定我们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今有了方向与目标,因为我们的生活,与众不同,却绝不残缺。
芭波和保罗如今为了摄制一部纪录片---《自闭已成人》 (Autism All Grown Up) ,正着手一次长达一年的环澳大利亚摩托骑行,影片将调查成人自闭症患者所面临的困难。